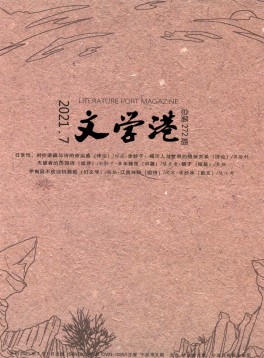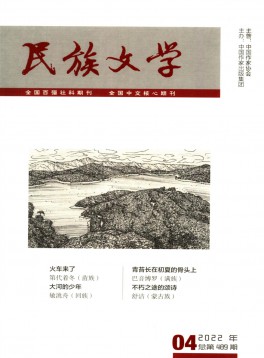文學批評論文模板(10篇)
時間:2023-03-20 16:26:26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學批評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本體建構:語言轉向條件下文學本體的倡揚
如果說“五四”以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借鑒“新批評”的語言觀,從而引發了對于傳統載體論語言觀的反思,那么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則實現了本體論語言觀的建構。20世紀80年代,“新批評”思想卷土重來,文學語言形式的研究仍是文學批評的焦點。“新批評”倡導對文本進行語義分析,主張文本細讀,從而使文學批評回到文學語言形式本身。這一理論的重申大大拓寬了中國文學批評家的理論視野,新時期的批評家反思傳統的載體論語言觀,開始從本體論的高度定位文學語言,不僅表現在批評實踐上,還表現在具體的文學創作實踐中,從而掀起了“語言本體論”的熱潮。從“新批評”與中國文學批評本體論語言觀建構的關系來看,“文學本體論”的理論來源于“新批評”。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陸續地翻譯、介紹“新批評”的相關理論和批評家。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于“新批評”的翻譯、介紹與研究呈現出系統化、規模化態勢,其中楊周翰、趙毅衡等是重要代表。他們撰書立著和發表重要論文,介紹和傳播“新批評”理論。趙毅衡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當時國內研究“新批評”的扛鼎之作《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對“新批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另外,還陸續出現一批“新批評”的譯介,如劉象愚翻譯的《文學理論》、趙毅衡編譯的《“新批評”文集》等,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新批評”的知識譜系。后來有評論家稱:“英美‘新批評’派的文學本體論是我國文學理論最近幾年來出現的文學本體論的來源之一,國內的文學本體論的呼喚者也自覺地向‘新批評’派尋覓理論武器。”[4]從此處可以得知,中國文學批評呼喚語言本體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有極大的關聯。“新批評”的價值,在于為中國文學批評回歸本體提供了理論資源,但是,它不是通過自身的理論體系來證明的,而是通過對統治中國已久的反映論的批判來實現的。其次,“新批評”本體論語言觀是對“反映論”的糾偏,是對載體論語言觀的顛覆。自“五四”以來,一直統治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是反映論的文藝觀。“反映論”與“新批評”的文學本體論最為抵牾,“文藝觀是反映論的,這被認為與新批評的本體論主張截然對立”[5]69。在此基礎上,“新批評”作為一種“清道夫”式的文論,主要的使命是擾亂學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們對傳統反映論文藝觀的懷疑,對載體論語言觀的批判。因此,“新批評”的存在意義是通過對“反映論”一統天下的局面的批判,打破文學批評界的既定秩序,使人們對權威和傳統產生懷疑,為中西文論的融合開拓空間。故而,“新批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界的重要價值:一方面,憑借“文學本體論”闡釋文學語言在文學中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通過批判“反映論”,建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新秩序。基于以上兩個原因,在“新批評”的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批判了載體論的語言觀,轉而關注文學語言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建構本體論的語言觀。在進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時,對于文學的本體究竟是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大體經過了由“作品本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變。“作品本體論”以作品為核心,其主要理論內涵是文學活動以作品為重,文學批評應面對作品本身,深入作品內部進行研究,才可窺見文學的本質,文學研究與作者、世界、讀者等無關。持“作品本體論”的批評家主要有陳曉明、胡經之等。“作品本體論”的觀念主要來自“新批評”的韋勒克(RenéWellek)。由于受西方現代語言學派的影響,不難看出“作品本體論”中包含著“語言本體論”的影子。“語言本體論”的一派則以語言為旨歸,高揚文學語言的本體價值。1985年底,黃子平撰文《得意莫忘言》,提出了須重視文學語言本身的價值,“文學作品以其獨特的語言結構提醒我們:它自身的價值。不要到語言的‘后面’去尋找本來就存在于語言之中的線索。”[6]這既是對文學語言的本體意義的強調,也是對傳統的語言載體論、工具論的有力批判。李劼也在他的《試論文學形式的本體意味》一文中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所謂文學,在其本體意義上,首先是文學語言的創作,然后才可能帶來其他別的什么。由于文學語言之于文學的這種本質性,形式結構的構成也就具有了本體性的意義。”[7]“語言本體論”將把語言與形式合二為一,形式是內容化了的形式,內容溶解在形式之中,語言建構了文學的本質,建構了人類世界,批判了語言意識薄弱的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在文學創作界,20世紀80年代的作家們也開始秉持本體論的語言觀。語言在文學創作中不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承載內容的載體。語言就是文學本身,是文學的本體,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語言與內容相互依存、融為一體,文學創作的生命就是語言革新。在“文學本體論”大討論背景下涌現出的一大批作家表現出了對于語言形式創新的關注。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余華的先鋒系列小說、于堅的詩歌,都醉心于語言的革新。他們以語言形式的創新為文學創作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空間。作家們不僅在創作實踐中關注語言,而且在批評實踐上也闡發了他們對語言意識的重視。汪曾祺提出:“中國作家現在很重視語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語言不只是一種形式,一種手段,應該提到內容的高度來認識語言不是外部的東西。它是和內容(思想)同時存在,不可剝離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語言。”[8]1從汪曾祺的這段話看來,語言于文學處于顯要的地位,而當時創作界對語言開始充分地重視,其語言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20世紀8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界和文學創作界共同致力于語言意識的轉變,文學語言觀由語言載體論轉向語言本體論,為文學語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打下了基礎。“新批評”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與其說二十世紀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不如說二十世紀是一個以本體論批評為主調的時代”[9]。而西方各種文論在中國的“理論旅行”或多或少暗藏著“新批評”的潛流,“盡管在它之后,西方還涌現了諸如結構主義批評、原型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等等批評流派,但這些批評流派在形式本體的意義上基本都是沿著‘新批評’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發展”[9]。因而,“文學本體論”大討論的意義在于,它確立了文學語言的本體地位,實現了從語言載體論到語言本體論的轉向,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既有型態,促進了文學語言觀念的全面變化,推動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新的語言范式的建立。但是,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大討論只是一種理論倡導,給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提供了一種文學研究的新途徑,即從文學內部、文學形式來探討文學,卻未建構一個完整的理論系統。無論是“作品本體論”還是“語言本體論”,都是文學研究的一種中介,旨在將已被割裂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連接起來。被“新批評”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在理論重構過程中,遮蔽了“新批評”自身的理論豐富性,“新批評”被后世所詬病的“文本”自足性、“文本細讀”法等也漸漸地與“文學本體論”大討論之后中國的理論氛圍格格不入,故而注定了“新批評”與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只是暫時的“親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文學本體論”大討論沒有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走向“本體論”,而是最終走向了“主體論”。
篇2
二、后結構主義、福柯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
新歷史主義作為后結構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其理論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后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一方面,先前歷史主義對歷史語境的重視在新歷史主義的方法中得到了承繼;另一方面,后結構主義對歷史意義的消解又被新歷史主義借用來突破既有的歷史敘述。這樣一來,新歷史主義不可避免地秉承了后結構主義的一些重要思想。歷史總是被敘述出來的,因此對“過去歷史事件”的第一手把握或者最直接的感受已經不可能了。沒有一個統一的、前后一致的、和諧連貫的、大寫的單數“歷史”(History)或者“文化”。所謂的歷史其實是“斷斷續續充滿矛盾”的歷史敘述,這個“歷史”是小寫的,是以復數形式(histories)出現的。不可能對歷史進行任何“置身于其外”的“客觀”分析,對過去的重建只能基于現存的文本,而這些文本是“我們依據我們自己的特殊的歷史關懷來予以構建的”。一切歷史文本都應當得到重視,其中包括“非文學”的歷史文獻:一切文本或者文獻都體現出文本的特性,它們相互都是互文關系,對文學研究都有幫助。新歷史主義的文學觀、文化觀同時也受到法國的結構主義思想家阿爾都塞、伊格爾頓以及福柯等人的哲學思想的深刻影響。其中,福柯的哲學思想對新歷史主義影響最為深刻。福柯指出:“文化”歸根結底是具有“文本”特征的,而語言表達同樣也是話語實踐或認知的產物,其無法預知的斷裂(rup-tures)也就成為了一個歷史階段思維的主導方式。由話語產生的“權力微觀物理學”編織成一張關系網,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統網入眾多互不相關的局部沖突之中,使個人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懲戒機制中的懲罰者和被懲罰者。所謂“真理”其實是權利關系的產物,具有意識形態性。此外,福柯認為對于歷史的學習至關重要: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忘卻歷史,歷史所謂的完整性和延續性只是一種幻想,而實際存在的歷史往往只不過是互不相關的話語碎片。這些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指導了新歷史主義的歷史觀。福柯對于文學研究的重新界定和他的文化觀成為了新歷史主義重要批評共識之一。在關注福柯對于新歷史主義的重要影響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盡管福柯對權力運行模式、自我監管和對文化、歷史、意識形態三者之間的關系的闡述為新歷史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新歷史主義絕對不是福柯理論的延伸,也絕不是對于福柯理論的精細化演示。
篇3
二、沐浴在清潔理論思想下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的春天不應該是寂靜無聲的,死氣沉沉的;她的春天應該是萬物復蘇的,生機盎然的。美國海洋女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早在其《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書中,通過描寫一個綠色美麗的小鎮由于生態環境遭受人類社會嚴重污染而淪為一個黑色死亡之鎮的生態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態系統正在被人類的生產和生存活動而破壞的現象,因為殺蟲劑DDT等農藥的濫用使得地球環境受到了長期的危害,使得人類生存也受到了相應的威脅,人與大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和諧,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們生活在一個無處可逃的有毒廢棄物、酸雨和各種導致內分泌紊亂的有毒化學物質污染的世界了,這些物質影響了生態界性激素的正常機能,使雄性的魚和鳥逐漸變性。城市的空氣里混合著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許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農業經濟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徹底破壞,谷物的生長完全需要依賴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飼料喂養牲畜,造成了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崩潰的瘋牛病,而后又再次傳播給人類。”英國生態批評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喬納森貝特(JonathanBate)教授對生態社會的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個健康綠色和諧的生態社會不僅是一個無污染的清新干凈的世界,更是一個沒有等級壓迫和奴役的綠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女性與自然本身之間的聯系,另一種是人類社會對婦女統治和對自然統治的關系。生態主義者只能孤軍奮戰,為反抗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遭遇了各種艱難險阻,為爭取人與自然的平等之路變得十分艱辛。而“女性主義在運動初期,平等問題是女性思想關注的中心。當時的中產階級女性,受當時社會革命潮流的沖擊,她們從自身的感受出發,對束縛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種現象進行抨擊,鮮明地樹立起女性擺脫束縛的旗幟。”同樣,女性主義運動也由于“勢單力薄”,在反抗男權,爭取解放的道路上,會遇到紛繁復雜的斗爭形式,這樣,反抗之路就會變得更加漫長,勝利的希望就會愈發渺茫。雖然女性主義運動經歷了幾個世紀,確實發展和壯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軍”,建立統一戰線,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獲取最終的勝利。可以說“自然環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權社會運動中最好的“閨蜜”,生態女性主義者正是從綠色生態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權社會里不平等和被壓迫的現狀,用全新的雙重視角和戰略的眼光,審視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處,將這對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結合,開辟出了一條新型的可持續發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態女性主義批評文學是一種新型的“綠色清潔”文學批評,是生態主義蓬勃發展的生動體現,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對女性主義文學的新角度的闡釋。如果說生態主義運動是生態主義者保護自然的綠色運動,那么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之路就是女性主義者用綠色理論捍衛自己合法權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篇4
20世紀是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大發展的世紀。受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影響,文學研究過多地局限于語言和文本現象,熱衷于對形式、文體、技巧等實證、實用性的研究,而忽視了文學的道德教化功能。環境問題、社會問題乃至人類的精神問題的復雜多樣化促使文學研究重新關注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類自身的精神訴求。20世紀80年代,西方文學評論界開始逐漸由集中注意研究語言本身及其性質的能力(內部研究)轉移到注意研究語言同上帝、自然、社會、歷史等被看作是語言之外的事物的關系[1]。20世紀90年代,作為生態批評支流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迅速成為西方文藝評論界的“新星”。
一、生態危機: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契機
現代工業的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早在19世紀已經引起人類的注意并開展形式多樣的環保行動。20世紀50年代中葉,以“公害事件”為代表的環境問題,引起世人的更為廣泛關注,人們意識到環境污染嚴重損害公眾健康,并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從而爆發了一場新的社會運動——生態運動。生態主義者反思人類行為,質疑啟蒙時代以來的理性至上論,揭示人類中心主義才是生存危機的根源。為探求人類的出路,生態主義圍繞非人類的道德身份展開爭論,形成形式多樣的環境倫理。
生態女性主義是環境倫理中的最新發展,是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結合。一百多年以來,女性主義經歷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20年代的以要求平等的政治經濟和受教育權利為特征的自由女性主義,和20世紀20—60年代的以爭取女性社會文化身份為特征的激進女性主義的洗禮。在生態危機和環保運動的激勵下,在婦女參與環保運動的實踐基礎上,生態女性主義于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蓬勃發展起來。它借助解構主義,深入挖掘當下生存危機根源——父權制的男性中心主義觀并進行顛覆性批判,力圖構建一種新的環境倫理文化,為人類的持續謀求出路。
二、新倫理文化的建構:生態女性主義的活力源泉
人類社會經歷了從人類初始階段對自然界的尊崇、恐懼、依附的生存意識(即自然倫理階段),到對自然的改造而使自然環境從人類生存視野中逐漸隱退后的對社會利益的關注(即社會倫理階段),再到現今環境問題帶來生存危機而反思后的尊重、愛護自然,尋求人與其他萬物平等依存(即環境倫理階段)的倫理認知和革新過程。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倫理道德的修整重構過程。生態女性主義正是生態語境下倫理革新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廣泛借鑒其他流派思想,特別是生態思想和傳統女性主義思想,批判父權文化體制下的二元對立價值等級思維模式和工具理性主義傳統,以顛覆西方主流的父權——男性中心主義倫理觀,并形成一系列具有自身特點的倫理價值體系。
首先,它追求整體和諧和生命解放,反對壓迫。對“各種形式的統治和壓迫相互交織”[2]的認同是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基點。在肯定自然界獨立的內在價值,賦予所有非人類(如動植物、河流、山川等)同等的道德地位,關注所有與自然——心理、性、人類和非人類——有關的統治同時,生態女性主義反對各種社會統治形式(種族、階級、年齡歧視及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將所有被父權文化貶為他者的邊緣弱勢群體如女性、黑色人種、同性戀、酷兒(queer)等視為盟友,認為沒有自然的解放,沒有其他邊緣群體的解放,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從而將其倫理關照的對象擴大到最廣闊的領域。
其次,它吸收生態批評的整體性觀念,尊重差異,贊美多樣化,認為差異、多樣性是生態系統和諧穩定的保障。其多樣性既包括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又包括人類個體的個性和社會生活風格及地方風俗的多樣性等。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對物種的侵害控制,致使生物簡化。現代商業社會的技術和競爭將人異化為失去生氣和個性的生產機器。在技術和利益的驅使下,統一的文化觀念和文化方式無孔不入,誘導現代人的拜物心理,泯滅人的個性,使社會生活風格“齊一化”,文化也因簡化失去其多樣性魅力。
第三,它呼吁建立一種基于互惠和責任原則而非統治原則的生態倫理觀,強調感性如關愛、尊重和公正的倫理價值。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人類與非人類存在物的關聯性,從女性與自然在生理、心理和體驗上的關聯出發,提出重新界定人類自我的身份,拋棄以人類——男性為中心的抽象獨立自我的主人身份形象,代之以生態的關聯自我[3]。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人類只有意識到自己與世界萬物千絲萬縷的聯系,才能從根本上關注“他者”,以平等的道德權利持有者身份修正自己的不良行為和思維方式,還“他者”公正,尊重和關愛“他者”。唯如此,人類和自然才能和諧相處。
生態女性主義者不僅多角度解構父權制思想,還多層面建構新倫理文化。一些女性主義者以恢復對月亮、地球等的女神崇拜儀式來贊美女性與自然的聯系,并用人類學家對史前期的母系社會的考古發現論證女性文化建構的可能。普魯姆伍德提出重新闡釋大地女神蓋亞,認為認可地球的母親身份有助于人類尊重和關愛地球及其上的所有存在物,有利于形成新的倫理道德觀。一些激進的女性主義者對基督教神學進行改造,把上帝理解為母親或女性。溫德爾把上帝稱為我們的母親,因為“上帝的父親形象適用于父權制社會中的人格形成”[4]。沃倫根據IrisYoung對傳統分配模式的社會公正性的剖析,探討基于該分配模式的環境公正性,指出由于傳統的分配模式是靜態的物質傾向的,不重視社會進程中的社會關系,因而無法對生態群(如物種、數量、自然棲息地等)的狀況給予足夠關注,無法建構“生態的關聯自我”,也不能充分重視并體現關愛和尊重的重要價值,只有非分配模式語境才是適合生態道德生長的土壤[5]。這些頗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倫理文化設想,為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開拓了新空間。
三、生態女性主義: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某種反映,是人類理解自己的生產勞動及世界的一種形式,是為滿足人類道德情感或觀念表達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富有特點和不可替代的道德思考形式”[6]。因而有人認為“真正的藝術和批評服務于一種道德目的”[7]。以反思人類思維方式、規范人類行為并以最終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為己任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潮,其倫理特性必然從社會層面延伸到精神層面,從對現實社會中的道德現象的評價和規范及對其倫理根源挖掘延伸到文學批評領域,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它遵照生態女性主義倫理道德觀念,將性別(女性)和自然結合起來探討文學。它在關注人倫道德的同時注重弘揚生態倫理道德,成為文學倫理學批評的新視角。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學與女性及自然環境關系的研究。大體而言,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透過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棱鏡來閱讀文學文本,使文學文本中那些以前忽視的要素凸現甚或更為顯眼,促使文學批評家對文本的傳統要素如風格、結構、修辭和敘述,形式和內容有新的發現,加強探討文本中不同角色——人類與自然之間,文化與自然之間,不同種族、階級、性別、性取向的人之間——的聯系與差別,探討影響人類與自然,人們相互之間關系的差異與聯系的因素[8]7。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批評家必然會提出這樣一些基本問題:自然和女性在這部作品中是如何再現的(是次等的、低級的、破壞性的、缺乏理性的還是美麗的、充滿慈愛溫情的、不可缺少的),自然和女性在作品中扮演著何種角色(是受貶抑的、受支配的、工具性的還是平等的、受尊重的、具有自身獨立價值的),自然和女性之間的關聯性是如何在作品中體現的,以及作品中表現的倫理價值觀與生態智慧是否一致等。而一部具有生態女性主義意識的作品,往往符合如下標準:即是否體現整體的關聯性;是否體現對男女、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整體和諧、多樣而相互依存關系的追求;是否反映對兩性之間、人與人之間以及人對自然的征服、支配、壓迫和統治等問題的探討;是否有助于重新認識人與其他萬物的關系;是否有助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的和諧關系;是否有助于警醒世人,倡導生態智慧,喚起人們的生態意識等。
生態女性主義在從文化哲學領域切入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和人文學者承擔文學批評的責任,以發展一種文學批評體系來反映和促進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政治目的,這一責任是以文本閱讀為基礎的。首先,通過閱讀各個時期的文學文本,揭示文學作品中反映的自然與女性的關聯,探尋在文學領域中對女性對自然兩種統治和壓迫的歷史文化根源。生態女性主義神學者對《圣經》進行對抗性閱讀,批判它借上帝之口確立男性對女性和自然雙重統治和奴役的地位而成為父權——男性中心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次,通過重讀文本,得出新的結論,以改變傳統的文學史,重建文學經典。一方面,將被忽視的被埋沒的體現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的文本,尤其是女性文本重新評價,納入經典之列,如一些寄情花草而被貶為閨閣之作的女性文本得到認可,曾被嘲諷為無病的美國女海洋生物學家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更是以其女性的細心觀察和細膩描述被譽為文學、女性、自然三者完美結合的典范;另一方面,重新審視以往經典文本,頌揚體現整體關聯的、洋溢著關懷同情、慈愛溫情的作品;抨擊體現父權中心的、工具理性的、擴張性的、彌漫著男性支配和控制欲望的作品,否定其經典地位。如:被奉為個人英雄主義經典的《魯濱孫漂流記》體現崇尚權力、征服、統治和男性工具理性而被批判;而珍妮·斯梅雷的《千畝農田》、斯坦因貝克的《憤怒的葡萄》等,因其探索了科技在人類貪欲支配下給土地所造成的損失,以及人的身體、特別是女性的身體與土地的緊密聯系,揭示了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和征服的悲劇局面,體現了生態女性主義思想。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上,努力發掘該文類的寫作特征,總結和建構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從而修正傳統文學的價值取向[9]。這一方面可以帶領文學創作者認知、關照、表現社會生活、世俗人生,進行文學創作,深化文學的審美價值;另一方面引導讀者的文學欣賞,通過發揮典型人物的啟示作用和“揭丑”文學的警醒作用,影響人們的文學乃至文化“消費”觀,改變人們行為方式,從而實現文學的社會教化功能。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并非否定所有其他形式的批評。它以新的批評尺度為文學倫理批評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它借助文學宣傳生態女性主義,倡導生態智慧,強化環境意識;它不僅重新釋義文本,還積極推動社會和人生的建構;它弘揚關愛、平等公正、聯系依存的生態倫理觀,不僅有利于促進建立人與自然、男人與女人自然和諧關系,也有助于推進各“亞”文化群,如有色人種文學、黑人文學、少數族裔文學、流散文學(diasporicliterature)等從邊緣走向被關注的中心,使人類聽到不同的聲音,從而最終建立“一個免除了有害物質和生態災難威脅的社會……一個免除了壓迫和毒害的社會,一個免除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毒害的”[10])生態社會。
[參考文獻]
[1]魯樞元.生態文藝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71.
[2]Brown,Rachel.RightingEcofeministEthics:TheScopeandUseofMoralEntitlement[J].EnvironmentalEthics,2004(26):247-265.
[3]Gaard,Greta.EcofeminismandWilderness[J].EnvironmentalEthics,1997,(19):5-24.
[4]何懷宏.生態倫理—精神資源與哲學基礎[M].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194.
[5]Warren,KarenJ.EnvironmentalJustice:SomeEcofeministWorriesaboutaDistributiveModel[J].EnvironmentalEthics,1999,(21):151-161.
[6]聶珍釗.關于文學倫理學批評[J].外國文學研究,2005,(1):8-11.
[7]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批評方法新探索[J].外國文學研究,2004,(5):16-20.
篇5
二、讓學生了解適度批評的重要性
在課程教學中,應該讓學生充分明白學前教育中,兒童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應該認真了解兒童行為的原因,有許多行為是這個年齡段孩子特有的,教師不應對兒童進行深度批評,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這樣的行為再次發生。應該循循善誘,用平和的語言告訴兒童,這樣行為的錯誤性和這樣的行為長期下來會造成的結果,在對兒童進行講解之后,可以做出一種期望或向兒童指明如果再次發生就會得到什么樣的教訓。教師要認識到學前教育中批評不需要謾罵與侮辱,教師對幼兒要該獎則講、該罰則罰,獎懲并濟且獎懲適度,強化兒童的良好行為,抑制兒童的不良行為。課堂中,老師可以通過講解各種學前教育中教師對學生過度批評的案例,通過各種新聞、社會調查結果、調查報告等,告誡學生對幼兒深度批評的負面影響,并以此引導學生掌握批評的度。
篇6
中圖分類號:G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6-0273-02
詹姆遜對西方社會文化狀態和社會矛盾狀態的分析和批判對于我們研究文學和全面地分析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陳煬,2004)。詹姆遜正是由于運用的辯證批判方法,才能開拓出從社會意識形態的的視角解讀文學文本的方法。同時詹姆遜對后現代的研究側重于資本主義系統本身,更具體地說,從生產方式和商業化的角度注重文學實踐,是詹姆遜文學批評的重要特征。分析這些矛盾,推測其發展趨勢以求得對現實的深刻認識。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將從話語分析的視角以社會意識形態和商業化研究手法為基礎來全面闡述后現代文學批判性。
詹姆遜認為對后現代主義文學分析必須與晚期資本主義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發展的經濟和商業化特征聯系起來。基于此,我們通過分析其中的矛盾和沖突來全新地展示后現代文學對現實的批判視角。詹姆遜成功地將意識形態和商業化的分析手法運用到文學批評實踐中,采用細致的文本話語分析實現文本研究與社會分析的結合。因此文學批評必須重返意識形態的陣地(胡亞敏,2003),直面權力和控制等社會問題來解讀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學實踐。在后現代背景下,后現代文學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資本主義的商業化社會現狀相結合(藍水,2005),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商業化分析的視角對于文學研究來說可謂是一種內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們借鑒于此進一步在話語分析中全面展開對后現代文學批判的分析和展示,開辟出文學與社會意識形態和商業化方式通過話語分析相聯系的新途徑以便更加徹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復雜的社會實踐(孫 輝,2005)。
后現代文學批判的目的應該致力于揭示出意識形態企圖掩藏或超越的東西,通過話語分析維護和堅持既定意識形態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錯誤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們在進行后現代文學研究時要完整的理解意識形態批判的內容和任務,就必須建立一種與文學話語分析相結合的意識形態理論批判方法,從而對后現代文學批判進行新的闡釋(Douglas,1989)。后現代文學話語分析的重要性就體現在可以如實的反映和實現意識形態功能對后現代社會進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這必然會在《小大亨》的話語分析中得到充分體現。借鑒于此,我們具體闡釋《小大亨》的話語分析和實踐是如何行使其意識形態功能的,從而幫助我們理解,體驗諸種種文學敘事創造或編撰的被抑制的現實,揭示或闡明世界(胡亞敏,2002)以體現后現代文學的批判視角。
從斯特拉的意見中可以看出愛德華是絕對有能力跟科恩商談和處理關于財產繼承的相關法律事務。而巴斯特姑媽朱莉婭和安妮卻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見,堅持愛德華的父親詹姆士來全權徹底處理所有的相關事宜。當斯特拉提及到愛德華應該自己跟科恩商談出生證明和簽署合同的相關事務時,姑媽們對此意見提出了強烈的反對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行動權,這就表明了在后現代傳統家庭中長輩的權威和統治地位是絕對不允許動搖的。在這種家庭等級意識形態的控制和影響下,愛德華在其父親過問財產繼承事務之前根本沒有權力參與或咨詢。這也是姑媽們不同意也不允許他跟科恩討論和磋商具體細節的真實意圖之所在。事實上這已經清晰地表現出兩種意識形態的沖突和矛盾,談話中的平等關系無法確定,自由對話的空間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話語分析我們可以從社會意識形態的視角窺見和挖掘后現代社會實踐中固有的,內在的矛盾沖突和根深蒂固的傳統教條和觀念,更重要的是評價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識表象中虛偽和欺騙性的本質,從而抵制潛在的真實意圖。這恰如其分地解釋到文學批評從意識形態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亞敏,2003),可以直接面對曾經在意識形態領域里被忽視的社會實踐中的權力和控制。通過話語分析我們我們清晰看到《小大亨》中處于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將如何使自身權力立場合法化的各種策略, 而處于對立面的意識形態則往往采取隱蔽的策略力圖對抗和破壞主導價值體系。因此在話語分析這個層面上,《小大亨》中的話語實踐成為顯而易見的充滿意識形態的手段,成為社會實踐象征的策略。在此種情況下話語分析可以幫助我們挖掘文學文本中潛在的意識形態蹤跡和展現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以此來體現后現代文學的批判視角。
立足于西方變化著的社會現實,后現代文學批評也就必然主張通過話語分析的手法對文本中影射的社會矛盾和狀況進行批判性分析,推測其發展趨勢,以求得對現實的深刻認識(藍水, 2005)。后現代文學實踐與市場體系和商品形式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后現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邏輯全面滲入文學領域,為此,通過文學批評作用于現實,這也是后現代文學研究和實踐的動因和目的,由此我們將從商業化分析的視角以話語分析的手法來全面展現小說《小大亨》中的文學批判視角。接下來我們以克勞雷,朱伯特的學生們之間的對話為例來分析證實資本主義商業運作是以資本增殖為導向的。
――什么是委托書?
――股票委托書?哦?我想孩子們最好你們先要知道一點關于蘋果的價錢的常識,然后再談這個問題,能跟上我的思路嗎?現在首先,從總體上來看股票市場是什么呢,無論如何,那就是將需要購買的一方與將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現在如果你在銷售什么商品,明確的東西…… 他用手比劃成一個籃子, 讓我們假設是籃子。你應該可以發現想找到這種籃子的買家的確是一件相當有難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擁有制造籃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馬上將其出售。總是有買家在某處等待著,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認識,也沒有必要看到他是誰,你們知道我在說什么嗎?
――是的這些籃子又怎樣呢?如果假設這家制造籃子的公司自己都無法銷售商品時?
――好的,我們只好馬上開始談談古老的供求規律,不是嗎,他們大概首先不會開始生產籃子除非……
――他們都因為自己生產的籃子沒有人購買而陷入困境,那么誰還想購買他們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這樣就會導致股票價格的下跌,是嗎,那么古老的規律……
――那么這種古老的供應和衰落法則伴隨著籃子的滯銷對于他們的股票又有什么區別呢?好似任何人買賣股票都是為了急于拋售他,那么人們怎樣知道它的價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這些紙張扔到地板上一樣,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干什么,那么我們用自己的錢購買了鉆石電纜的股票而如果沒有人愿意購買電纜時該怎么辦,就好似沒有人購買滯銷的籃子一樣,其結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爛手中的股票紙然后扔在地板上,這將意味著什么?
-等等現在,等等。首先,你們將不會被鉆石股票套牢,請相信我所說的話。第二點,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個工作人員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認識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著什么。還有第三點,股票的價格不會是毫無控制的,就象你們所說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員,外邊正在進行交易工作的專業人士,很多人都稱的上是專家……(P84-85引文為筆者試譯)
學生們首先就什么是委托書展開提問,然而克勞雷就直接將話題轉移到商品的價錢上并以籃子的業務為例進一步闡述了在股票市場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買與賣,其被認為是促進商品流通和交換的平臺。但是學生們馬上就反問到如果生產的籃子不能銷售該怎么辦,而克勞雷打著供求關系規律的幌子相應地進行解釋完全無視市場上真正的需要。因此這樣的解釋將必然更使學生們感到困惑不解,他們的疑問是誰將會購買和操作這種商品的股票如果其產品本身都無法銷售,這樣也必然會引起股票價格的下跌。學生們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單純地股票的買與賣,更為重要的是,想探詢股票的真正價值,股票的買賣并不是盲目的跟風,因此他們相當清楚購買鉆石電纜的股票并不是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資股票的真正價值。最后克勞雷也無法給出合理的解釋只是保證他們將不會被鉆石電纜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強調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員十分清楚他們在做什么,他們的強項就是擅長進行股票交易。為了設法勸解學生們確信購買股票的益處,他進一步解釋到股價是被那些在股市中發揮著積極和決定性作用的專家們所控制的。上述話語分析主要是圍繞著美國商業活動展開的,我們看到商業化的已經從最大程度上轉變為標準化的動機,內在的資本邏輯已經在商業活動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話語實踐反射出資本運作的新特點,這也有力地證明話語分析和資本商業化的背景相結合提供了一種分析后現代美國社會潛在社會矛盾的全新的徹底清晰的洞察視角,更加明確地以診斷的眼光來辨析資本的商業化邏輯和復雜的商業現象。我們注意到文學話語分析從商業化的視角已經成為展示后現代社會商業實踐的有效途徑和策略,從中我們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現代美國社會中大公司賺錢的渠道和捷徑就是通過靠欺詐和投機,這正說明了在后現代社會中資本家所關心的是商品和資本的流通和循環而不是生產。因此后現代文學批判緊密地跟商業化的邏輯視角相結合并且越來越受到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滲透和融合來展現后現代社會實踐的本質以體現文學話語實踐中的批判性。
詹姆遜的文學批評方式具有方法論的意義。通過對《小大亨》中的話語分析將后現代文學批判與這個時期所出現的種種社會意識功能和商業化因素聯系起來分析和研究后現代文學,從而致力于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批判資本主義現實世界。
參考文獻
[1]胡亞敏. 詹姆遜的文化轉向與批評實踐[J].第42卷第2 期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2).
[2]藍水,熊箏.后現代社會的文化轉向-論詹姆遜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N],湖北教育學院學報,2005,(5).
[3]李世濤.后現代文化理論建構中的批判性視角[J].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篇7
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界定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其次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必須弄清什么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關于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問題,時下呈現出兩種不同主張。第一種主張認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體育學學術成果,即把體育學學術成果當作批評的對象,主要對體育學學術成果進行評判,持這種主張的人為數不少,也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第二種主張是以整個體育學術活動體系(體育學學術實踐主體和體育學學術實踐的成果)作為批評的對象,它不但對體育學學術成果展開評判,還對體育學學術觀念、品格、環境、思潮、流派以及學術批評自身進行判析。我們比較贊同第二種主張,并傾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如下的界定: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包括學術主體、成果、理念、風格、思潮、流派、運動以及學術批評本身,即包括一切體育學學術活動系統。比如李力研“科學研究必須老老實實——因楊杰、周游兩作者而說的話”以作者(學術主體)為批評對象,盧元鎮“中國體育社會學科進展報告”以中國體育社會學學術成果為評判對象,趙山成“試論茅鵬的學術思想”以茅鵬及其學術思想為對象,黃卓“關于體育科研中的責任與道德問題”以學術責任和學術道德理念為對象,陸一帆“體育生物科學研究方法置疑與推敲”以學術方法為對象,張力為“研究報告評價標準的界定與聯想”以學術成果報告標準為對象,楊正云、王穎“論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校體育思潮的歷史變遷”以學校體育思潮為對象,王新、鐘明寶“芻論體育批評的含義及其形態”以體育學學術批評自身為對象等等。可見,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體育學術活動系統中各種具體學術現象,從科學的觀點出發,作出思想性、理論性及價值性諸方面的評價。從表面上看,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范圍如此界定,似乎與體育理論的研究對象基本同等。事實上,它們有較大的區別,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其自身顯著的特點。具象性所謂具象性特點,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是各種“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或者是一項成果,或者是一個或幾個學術成果主體,或者是一種學術思潮,或者是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或者是一種批評方法,或者是批評的主體等等。體育學學術批評正是對這些具體要素有針對性地予以研究。毫無疑問,體育學學術批評這種具體的局部研究當然也要聯系其它部分甚至體育學整體,但是,它是由具體而整體,其研究的中心始終是具體的體育學學術現象,也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局部微觀研究。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一個基本特點。集中性所謂集中性,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主要集中在“學術成果”這個基本要素上,也就是說,體育學學術批評是以“學術成果”作為體育學學術批評最基本的對象,其它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活動,如“體育學學術主體”批評、“體育學學術理念”批評、“體育學學術風格”批評、“體育學學術思潮”批評等,只不過是“學術成果批評”的延伸,或者說是在此基礎之上的批評對象的轉變。之所以如此立論,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體育學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系統各要素的核心,是體育學學術意識形態最常見、最基本、最直接、最活躍的形體和存在方式。體育學學術領域里的一切學術現象一旦離開了“體育學學術成果”這一具象形體,就無法存在,也就不稱其為體育學學術現象了。所以,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第二個特點是極具集中性。現代性所謂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現代性特征,是指體育學學術批評主要是以現實的、最新的多種多樣的體育學術現象為主要對象。盡管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偶爾會投射聚焦在過去某個歷史時期的一個點上,但這種偶爾的投射聚焦往往也是為了評介該對象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體育學學術批評是對當代現實體育學的研究,屬于一種共時性研究。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這種現實性特征,一是來自體育學理論發展的宏觀驅動,二是來自體育學學術批評價值的內在要求。因為體育學要發展,體育學學術批評要前進,都需要以新理論、新實踐、新成果為研究對象,也只有通過對開創新領域和出現新論斷的批評與評價,才能實現真義上的進步。所以說,“現實性”特征直接決定著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意義、價值和生命。由此,可以說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就是體育學術活動中各種具有一定新質的具體的體育學術現象。其中,最新的體育學術成果是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基本對象[3]。學科性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與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緊密相關,體育學學科內涵和外延的所有成果部分都應該是體育學術批評的對象,如果其內涵與外延超出體育學學科領域,則不應成為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因此,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具有學科性特點。這是體育學學術批評區別于其他批評的最顯著特征,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確立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時候,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第一,我們必須客觀、公正地面對各種體育學學術批評實踐,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而是主觀主義、片面主義當頭,偏于一隅,就可能使體育學術批評有失公允。第二,我們的研究必須是對體育學學術批評對象的全面整體的研究。如前所述,盡管我們對體育學學術批評的對象作了簡單、靜止、孤立的解說。但在體育實踐中,這些對象并不是簡單的、靜止的、孤立的,而是復雜的、運動的、龐大的、有機統一的系統整體,體育學學術批評必須把它作為一個系統整體予以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動態的而不是靜態的、系統的而不是孤立的研究。只有盡可能的全面真正地占有體育學學術批評的研究對象,才可能保障獨立建構體育學學術批評體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體育學學術批評的性質
篇8
二、文學修辭批評近當代史的縱觀特征
若以微觀與宏觀的兩極化來定義,宏觀或廣義上的文學批評,個體在文學作品閱讀過程,或閱讀行為終結后,由閱讀的文本而觸發的評價,包括感想、判斷等,都可視為文學批評。若從微觀或狹義上而言,文學作品的評價則要力求客觀與精確。這種學術活動,既可以針對某一具體文本,也可為一系列,即與某既定文本有“互文性”的文本。這時,文學理論或觀念的選擇支撐就變得舉足輕重,關鍵字眼落在了“學術性”。批評理論的選擇也就是批評視角與批評手法的選擇。論及批評手法,西方近當代文學承受過比較流行的,當屬社會批評、意識形態及文化批評。從宏觀切入,從宏觀著眼,從宏觀入手,對文學作品進行評價的操作,是這些手法的共有之處。坦誠地講,宏觀視野下的文學作品審視,有其過人之處,即透過現象,直取本質,對文學作品的認知可以直接由感性而上升為理性。這種審讀,留下的,是對原文本折射出來的哲理、現實最佳的評價。然而,事物總有兩面性。宏觀文學批評對原文本內容的脫離,及對原文本滲透出的美學意蘊的漠視,也是其短視之處。美學是個體閱讀過程中情感觸發的火線,而美學的接收,又離不開語言技術手段及語篇結構的分析,只有以此為保障,文學文本或文學語篇,其概念意義、社會意義、文化意義等語言表達效果的生成機制,方能為作為讀者的個體所捕捉。可以斷言的是,文學修辭批評既注重了文本表達的意義與效果,即作為產品的文本效應,也揭示了這種效果與意義生產的過程或機制。從這種意義上而言,文學修辭批評可視為一種微觀近距離下的文學批評。論述至此,有必要對這種文學批評手法的必要性做進一步的闡釋。杰姆遜,作為美國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倡導者,曾經直言,個體對既定文本的接受,有層次之分。即描述層、分析層和價值判斷層。所謂描述層,是指文本以語言為媒介,帶給閱讀者的經驗認知,甚至身臨其境般體驗作者生產文本時,字里行間的某種。分析層面,則意圖打開文本構造的神秘,包括了文本生產的理論支撐與手法。這個過程,邏輯思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最后一層,也是文本分析最為高級的一層,當屬對閱讀文本的價值評判。如一般意義上的劃分,保守抑或激進,有意義與否等。文章認為,修辭批評應屬于第二層面,即杰姆遜理論中的“分析層”,也是意識形態、社會批評等第三層面價值評判的根基。這就是文學修辭批評在文學批評中的不可或缺,也是避免與其他手法沖突的過人之處。可以這樣推理,語言解讀衍生文本解讀,并催生社會及文化解讀,程度可謂逐級攀升。確認這個過程,會讓文學修辭批評的結論言之鑿鑿,從而使學術性的文學批評客觀性、說服性得以保證。反之,缺乏具體文本分析的文學批評,其主觀性可見一斑,更難免落入“形而上”的思辨窠臼之中,或許也可能意味雋永,但總有一種漫無邊際之感。
文學批評的最低標準,或通俗地稱為合格的前提,在周國平(1999)看來,可從下列幾處入手。其一,批評者闡釋與評判的動機,首先緣于自身對待評價文本的興趣。這種愿望是激發的,而非完全自發的,即待評價的文本本身是外界刺激物,是施為者,令批評者產生了進行評判的沖動。這種沖動的迫切,不是出于對某種文學理論的應用。換言之,批評者無可厚非地首先是某個文本的消費者。其二,批評者自身的能力定向。他并非一名普通讀者,而應是巴赫金筆下的高級闡釋者,具有文學或藝術上的內在修為,具有一定程度的鑒賞力與判斷力。在描述其評判之際,對文本要有一定程度的把握與見解,知道自身的評判要把“鋼”應用到哪塊“刃”上。這個過程,當然要有學術性理論的支撐。概括地講,周先生的觀點認為,真正的批評家需具備的兩大基本素質,首先要為待評價的文本所吸引,并對其有熱情感。其二,批評者本身需有審美感、鑒賞力。若不具備這兩個基本條件,可以想象的是,一個不喜歡閱讀文本的“批評者”以何資格去評判文本?文本不僅是評判對象,也是依據,或是批評闡釋的發端。道理雖淺顯,卻又易于忽視。
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為時間點,基于這樣的考慮,西方文學修辭批評出現了幾點顯著的特征。其一,批評家理論試驗意圖明顯,即憑借國外某種文學批評的形式主義理論來評判文學作品。在文中分析闡釋的,不是原作者創作的描述,也不是作者自身主觀性的思想追求,而是在馬原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文學敘事及語言問題,是典型的對文學文本的解構主義,打破了傳統文學批評中的“作者中心論”。其二,文學修辭批評的視角愈加開拓,方向也更加細化明晰。傳統文學修辭批評一直囿于語篇結構、語言特色等分析,但在80年代中期及以后,文本性的修辭評判,以一種新鮮的血液,融入到此行列中來。敘事分析這一修辭視角,是這一先鋒代表。變化的對比性在于,新穎的敘事分析不僅出現在新潮的文學創作中,即使采用傳統敘事手法的文學文本,也在運用這一先鋒理論。
三、文學修辭批評的價值與趨向
篇9
[中圖分類號]I206.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4-0061-04
從學術增長點的角度看,文學經典似乎是一個學術話語;從基本的概念內涵方面看,它又是一個學術命題。雖然文學經典具有話語和命題兩重屬性,但是話語和命題不能等同起來,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進行相互之間的轉化和通約。如果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選擇以便較為確切地界定它的根本屬性的話,那么,文學經典當然是一個學術命題,而不是一個學術話語。
學術命題所包含的系列問題都具有邏輯關聯,這種邏輯關聯就是指從普遍性的思維規律出發,把各種問題(包括指代與潛在的意義等)放在“產生的必然性”和“發展的因果關系”中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中的技巧性、視角價值、語體風格等并不重要,至多也不過是文本意義上的修飾與裝扮作用,其目的無非是為了獲得某種寫作學意義上的閱讀效應而已。事實上,文學批評在這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成功(美其名曰批評的藝術)都被看作批評的意義與標準的話,只能說明我們不僅具有了不負責任的態度,而且已經遠離了批評的宗旨。
認知經典不意味著要直接進入有關文學的諸如表現技巧、審美范疇、創作個性、語言范式等一些客觀屬性特征,而是要在確立文學經典的原則性、方式方法上首先取得某種共識,以便在針對文學經典這一命題的學術交流過程中保持意義指向上的一致性。
任何形式的文學創造性都是相對于已經有過的文學現實與文學模式而言的,或是從表現技巧、表達方式以及結構風格等方面來完成,或是從思想領域、知識范疇以及精神體現等方面來完成,但是,創造性需要某種意義的指導和意義的指向,創造性這一行為本身決定不了(文學)經典的范疇屬性,因此,作為經典的作家或作品必然要有文化品位,必然要能夠創造性地給人類帶來某個“偉大的啟示”或是能夠完成某種“深刻的提示”。而想要做到這一點,針對創造性的意義前提以及意義指向就不能沒有。20世紀30年代的批評家陳銓這樣說:“大凡一個民族,到了文化相當的程度,大多數人漸漸就有一種或他種共同對人生的態度,這種態度,就是他們民族特性成熟的表示。后來,他們民族里有了偉大的思想家出來,把這種態度給了一種哲學的根據,垂為道德的教訓,然后這一種共同對人生的態度,便一天一天堅固不拔,成了全民族共同生活的標準。”①不管評論家對文學的期盼是出于文化性還是民族性,總而言之,他們在客觀上已經給我們描繪了文學經典這一命題的范疇屬性,即所謂的“創造性”。對于經典作家和經典作品來說,無非是指那種體現在文化性、民族性、哲學的根據、人生的態度等方面的創造性,而不是指那種技巧性、語言范式等方面的被個性因素隨意地形式化了的創造性。
相對而言,文學批評似乎具有更多的(批評)對象和更廣的范疇屬性,因為它所關注的方面或層面幾乎可以說是所有的,它可以針對一個“怪異的形象”與“離奇的故事”,也可以針對某種“別致的話語”和“敘述的角度”;它可以關注形式上的以及表層上的東西,也可以關注內容上的以及深層次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批評不是為了維護文學經典也不是為了抵制文學經典,總之,它不完全受制于文學經典。然而,對于文學批評的理解難道只能是“到此為止”了嗎?文學經典難道只能充當被文學批評用來“引據”、“例證”的一種“典故”嗎?或者說文學批評難道只能是文學經典的“旁觀者”和“看客”嗎?我們也許能夠從當今的文學批評界感受到這種情形的真實存在,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已經充分而又徹底地認識并實施了文學批評。作為一種行為的文學批評,它當然要關注諸如手段、方式、過程乃至對象等層面,但是任何一種行為,尤其是這種有目的、有意識的“研究”行為,總要有一種建構意義世界的企圖,總會必然地帶上“試圖賦予混亂的文化現象一種秩序化的企圖”。②正是由于這種“建構意義世界”和“秩序化”內在邏輯上的要求,才使文學批評同時具有了目的論意義和手段論意義這兩種屬性,也從而產生了作為一種操作行為的文學批評和作為一種研究對象的文學批評之間的區別問題。當我們思考有關文學經典與文學批評的關系時,所指的正就是這種“批評的批評”(或“文學批評研究”),它的內在邏輯則是建構文學的“意義世界”和文學的“秩序化”。正是從這個內在邏輯出發,文學經典才真正成為一個文學批評領域中的問題。
在那些被視為經典的文學作品中,不論從創作性角度看,還是從文化品位方面看,一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提出并證明了某個文學命題。例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使文學很好地實施了“揭示社會本質”這一命題,高爾基開創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這個命題,陀思妥耶夫斯基使文學在“解析人類的心靈世界”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卡夫卡給文學開創了一種全新的面向人類潛意識的“真實性”,魯迅的作品體現了“用文學來揭示國民性,并改造國民性”這樣一個命題,茅盾則改善了革命文學的“表現藝術”等。類似的作家、作品不僅提出了(盡管并不完全是帶有創造性的)文學命題,而且也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命題,因而它們成了經典。在文學批評中,批評家或者立足于某個已有的命題,通過引用材料(作家作品)來證明這個命題的“合法性”,或者通過分析、歸納推演出某個新的命題以引起人們的關注。因此,從內在邏輯方面看,文學經典與文學批評具有相同的“生產”方式。
文學批評的相對獨立性意味著文學批評不受經典的制約和束縛,并不意味著不需要針對經典的意義指涉。批評的方式不外乎兩種:或者是以開拓者的姿態來建構文學經典,或者是以維護者的身份來強調、證明已有的文學經典(這里的“文學經典”當然不是指特定的作家作品,而是一種“經典”意識,具體地說,就是有關文學的價值屬性以及對這種價值屬性的認同感)。文學的價值屬性是通過文學命題來傳達、表達的,例如“文學應當真實地反映社會生活并應當本質地揭示社會特征”是一個命題,而“文學是一種精巧的文字游戲和情感的調配藝術”也是一個命題。不同的命題體現了不同的價值屬性,但無論如何,文學批評總是在為某個命題服務,總是在替某個命題說話,盡管有各不相同的追求,但總得有所追求。從這個基本前提出發,文學批評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提出一個文學命題并對它進行說明和證明(提出的這個命題不完全是通過創新,更多的情況下是針對已經被前人提出過的命題);第二,針對文學現象中所體現出來的某個文學命題進行反駁和批判;第三,通過組織歸納眾多文學命題之間的相互關系(即命題邏輯),調整乃至改變人們的以及時代的、民族的思維方式以及價值體系。
文學經典當然不是一個死板而僵硬的符號,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完全建立在人的無意識的認知心理基礎之上,也不意味著它只是一個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化因素。實際上,文學經典是由于它很好地實施并完成了某個文學命題才成為了經典。經典的產生取決于命題的產生,產生命題的必然性決定了產生經典的必然性,也就是說,經典的合法性來自于命題的合法性。例如,“五四”時期出現了(或有人指出了)自由詩這個文學命題,能不能產生自由詩的文學經典首先要取決于自由詩這一命題的合法性,只有經過不斷的理論探索與創作實踐,并且當這種體式特征的詩歌能夠獲得社會與時代的必然性的價值認同之后(如《女神》),它就會成為經典。再如文學與政治的結合是一個命題,用文學來表現政治也是一個命題,如果在創作過程,能夠通過特定意識形態的崇高性所固有的普遍性魅力超越政治“話語”并且具有了新的力量,那么,它就會成為文學經典,這說明經典的產生實際上是一種對某個文學命題的有力證明與演示。單就時代特征而言,經典的產生與經典的價值往往以極其簡單的方式來顯現的。然而,某些經典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其原因正在于這些經典不僅僅能夠很好地實施某個個別的文學命題,而且還能夠邏輯地組織起、歸納起眾多文學命題之間的關系,并以此來影響不同時代的人們的意義世界和價值體系。如前蘇聯開創的“紅色經典”文學,能夠超越時代,始終煥發出巨大的力量,激勵人們向困難與命運抗爭,召喚人們從被物質奴役、操控的境地中改造過來獲得精神上的解放。它所體現出來的文學命題包括文學對思想感情凈化作用、文學的歷史使命感以及文學對現實生活的典型化理解等等。作為一種文學經典,它能夠將這些命題進行合理的、邏輯的組織與歸納,從而使各命題之間具有了某種關聯,使之成為一個體現了命題邏輯的統一體并最終確立出相應的價值觀念體系。
從內在邏輯出發,文學批評的原材料是各種各樣的文學命題,而不是千姿百態的創作現象和瞬息萬變的作家作品。通過對這些命題的邏輯證明力求使文學命題之間能夠具有一種邏輯上的相鄰性和因果聯系。如果說文學經典已經給我們很好地提供并展示了某些文學命題的話,那么,文學批評則是通過解釋與必要的證明來使這些命題走向規范性、秩序性、合法性,然后再構建出相應的邏輯命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文學批評必然要有一種內在的精神動力、精神氣質以及心理活動的速度、強度、方向等。文學批評意味著“一個批評家是以自己的氣質,以自己在文學、政治和宗教上的好惡來判斷同時代人的,他盡可能地把這些變為一種權威的方式”。③對于文學經典來說,潛在的價值指向與精神氣質是特定的,它并不依賴于闡發者的花里胡哨、機智巧妙的表述,而對于文學批評來說,體現出批評者的價值指向與精神氣質,則是批評家應有的責任,決不該以文本的寫作背景與文化語景為借口來消解經典中所固有的精神氣質與責任,甚至于推卸文學批評所應有的精神氣質與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經典是文學批評領域中的一個不可取代的核心問題。
雖然文學經典與文學批評是兩個概念,而且文學經典在字面上具有名詞特征,文學批評在字面上具有動詞特征,但是,這個動詞既是這個名詞的生成機制,也是這個名詞的作用方式。當辯證地看待這種關系并思考它們的范疇屬性時,這兩個概念的外在詞性特征就顯得并不那么重要了,因為它們都體現了一種對于文學命題秩序化、規范化的期盼心理。正是由于這個共同的期盼心理,它們之間是相互融通的。反過來說,文學經典與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互融通需要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它們都要有“為何而存在”的“生成的合法性”。開創經典也好,開創批評也好,意欲何為?從內在的邏輯方面看,必然要有一定的意義指向(即對于文學的理想化期盼)。如果說這個前提在客觀上很有可能會成為一個人為的設置的話,那么,不管設置的現實作用如何,設置也是必要的。
21世紀以來,文學批評逐步被視為一種寫作現象,針對這個寫作過程,人們所關注的不再是寫作者的意圖、立場、態度、傾向性等,而是寫作者在表述技術領域中的意志放縱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閱讀行為意義上的異質性。在語義匱乏、批評意圖(即寫作姿態)匱乏的情況下,放縱了的技術以及技術操作意志使文學批評逐步變成旨在玩味“所指”的一種游戲。那種針對文學命題而言的文學批評對象不僅被狂亂的表述技術搞得似是而非,而且也被商業化了的表述類別取而代之并走向邊緣。應當承認,經濟的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化的確使文學和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困境,如同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如今我們正處于“在一個沒有對象的世界里”,④但若在此基礎上認為,由于全球化不利于批評界強勢話語的確立,因而很難使文學經典參與到文學批評中,產生這種觀念才是一個真正令人沮喪的悲劇性現象。因為強勢話語與弱勢話語、批評的主流與次流、根本的問題與細節的問題不但說明不了文學的經典性問題,而且也說明不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發展問題,本質上不需要經典、不需要批評,卻偏要大談經典、大談批評,難道是因為在話語的“權力場”中爭強好勝的緣故,或者說是出于某些遮遮掩掩的動機和欲望來展示自己的“表演”能力?
如果說在目前的文學研究這一大的學科領域中還存在所謂的文學批評研究領域的話,那么,這種研究的旨趣、意義、目的等就是被神圣化、神秘化了的“正本清源”(即所謂的追求“歷史本真”)。當學術界習慣于所謂的“深入扎實的梳理”以及“原生態”的闡釋與說明時,這種“習慣于”便自然地變成了“熱衷于”,熱衷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學術性范疇,以致于人們不僅把詳盡、扎實的梳理當作惟一的價值取向與評判標準,而且還用一種政治傾向性姿態來無孔不入地諷刺那些曾經有過的意識形態性。例如“那種性質先行、結論先行和理論先行的文學史敘述模式,不僅漠視史料的價值,而且在根本上也缺乏追求歷史本真的學術旨趣”。⑤言外之意就是,具有“歷史本真”的研究只能是在不需要理論基礎、不需要性質分析、無須乎有何結論的情況下才可以進行。研究的意義只能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占有、分析和把握……并對其來龍去脈做出人合乎歷史實際的解釋”。⑥對于這種研究態勢的另一個說法就是“大話文藝”,一方面是在嚴肅地表述著思想的解放性與開放性,另一方面是無意識地體現著針對文學意義的消費心理與“戲說”心理。由于這樣的學術氣質與研究風度,經典問題已經從原來的經典化演變成了去經典化,去經典化不是為了再經典化,而是為了消解經典頭上的神圣之光,不使它成為“永不衰老的智慧的豐碑”。盡管以經典的變動性、建構性為由,人們完全可以將這種“不知所處”的經典置之于各取所需的合法性位置,但是,文學經典不完全等于文學經典問題,正如文學批評不完全等于文學批評研究一樣。所以,隨之而來的邏輯性的疑問則是:什么才是經典問題產生的合法性?難道僅僅是因為經典現象的緣故才產生了經典問題嗎?或者說所謂經典問題只不過是將各不相同的經典現象置于各不相同的語境當中并找出各自的合法性嗎?任何一種沒有價值指向與意義追求的分析與解釋,都會很容易地轉變為針對現實的妥協、接受、委曲求全,也很容易流落成為隔靴搔癢的“彎彎繞”、“不及物”以及“虛熱癥”,⑦最終將實用主義的心理與虛無主義的本體論巧妙地結合了起來,將產生文學經典問題的合法性排斥在外。總之,文學經典有沒有必要進入文學批評領域,這是一個很理性的問題,也是一個前提問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樣,僅僅只是把經典當作一個話語引入文學批評的文本之中是牽強附會的,也是缺乏責任倫理與邏輯意義的。
文學經典之所以成為文學批評中的一個問題,是因為它們潛在地有著共同的意義指向,這個指向就是文化的完美。所謂完美,正如阿諾德所說的那樣,“偉大的文化使者懷著大的熱情傳播時代最優秀的知識和思想,使之蔚然成風,使之傳到社會的上上下下、各個角落”。而“不可能是獨善其身,個人必須攜帶他人共同走向完美”。⑧另一方面,由于走向完美不可能以個性化、獨特性為標志的,所以,追求完美的實質是觀念性和體系性。
推而論之,人類的思想觀念在幾千年來的發展過程中并沒有多少令人鼓舞的質的飛躍,而且它的完善與進步并非依賴于人類的創新意識。所以,經典問題以及批評問題的實質是意識形態領域中所固有的斗爭性。用馬克斯•韋伯的話來說,就是通過“責任倫理”(包括提供可靠的材料、價值判斷、勇氣、態度等)來傳達 “信念倫理”(即正義感、信仰追求及世界觀等)。⑨
就目前的文學批評狀況而言,所謂的文學經典問題實際上是以經典現象的面目出現的,它的基本模式是:經典是一個現象,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則是文學批評不得不顧及的一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經典現象是違背了文學宗旨的一個偽命題,因為只要把經典看作是一個現象,這就意味著將經典置于諸如視角價值、互文性、可闡釋性等境地,隨之而來的便是自然地將文學批評演變成了大眾文化,將文學經典演變成了一個時尚話語。
經典問題一旦進入文學批評領域,自然就會引起“批評的批評”,要想使“批評的批評”有所作為,單憑針對當代文學批評現狀的印象是不夠的。事實上,敢于正視現狀,并理直氣壯地揭示當今文學批評虛假性的人是有的,譬如說“惡劣的相對主義的恣縱的享樂主義,則天經地義地成為流行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準則,混亂、淺薄、虛假和庸俗成為司空見慣的文化景觀”。⑩“今天,一個文學家,一個批評家,似乎‘讀書養氣’,接觸社會還不夠,而必須能夠講點‘被壓抑的現代性’,提倡一點‘人文精神’,標榜一點‘學術規范’,夾道歡迎‘全球化’、‘國際資本’,否則就什么也不是。”然而,出于冷漠與無賴的社會心理,印象也只不過是“而已”。隨之而來的便是批評家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的問題,批評的方向應當是什么、不應當是什么的問題,盡管當今的批評界乃至學術界確實有很多的呼喚、提倡以及指點,可是這種充滿了良知與責任感的呼喚所獲得的仍舊是空蕩蕩無人回應的孤寂。那種“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所有的人都能夠接受這一事實,例如“在現代(晚清到1949年),文人們可以進行‘實名制’寫作,盡管筆名亂起,暗箭亂飛,禁令不斷,傷痕累累,但性情固在,目標明確,智力健全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在今天(21世紀),筆名少了,暗箭少了,文章越寫越整齊了,但批評文章中作者個人的性情和目標越來越失落。惟一的進步,是批評家進銀行存錢,也必然和普通人一樣,采取‘實名制’。”不錯,目標和性情自然是批評的關鍵,可是,誰有誰的目標,誰有誰的性情,什么樣的人就會說什么樣的話,沒有理由認為并指責當今的人缺乏性情和目標。況且,性情和目標并不是招之即來的東西。問題在于在眾多的、琳瑯滿目的性情與目標當中,我們需要的是確立、選擇。而且不管以何種方式、何種原則進行選擇和確立,只要有選擇、有確立就勢必要有排他性,勢必要有包括方向性、政治立場、階級意識等方面的斗爭性與批判性。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體現出文學經典在文學批評領域中的生成的合法性與存在的價值意義。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意識,那么,所謂批評的批評不過是一種虛擬和一句空話,而文學經典問題也不過是一種裝腔作勢和一個點綴批評家們學術門面的一個招牌。
[注釋]
陳銓:《文學批評的新動向》,《戰國策》,1941年,第17期。
韋勒克,丁泓等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主潮》,四川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第326頁。
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70頁。
岡特•紹儀博爾德,宋祖良譯:《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頁。
吳秀明:《應當重視當代文學史料建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5期。
閻晶明:《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的癥候分析》,《文藝研究》(卷首語),2005年第9期。
馬修•阿諾德:《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0頁、第26頁。
篇10
文學批評作為文藝學的一個專門術語,是“五四”時期從西方譯介過來的。“批評”含有“裁定”“判斷”等意。俄國批評家別林斯基說:“批評淵源于一個希臘字,意思是“作出判斷”,因而,在廣義上說來,批評就是“判斷”。17世紀后期英國批評家德萊頓也曾說過:“批評最先由亞里士多德確立的,它的意思是指作出正確判斷所使用的標準。”德萊頓使“文學批評這個術語在英語中意義明確并逐漸為較多的人使用。”我國傳統的提法多講“文學評論”,古代也使用過“批評”的概念。如明萬歷年間刊刻的《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鐘伯敬先生批評水滸傳》等。此處的“批評”含義已與近代接近。文學批評作為學科是以~定的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為指導,以文學欣賞為基礎,以各種具體的文學現象(包括文學創作、文學接受和文學理論批評對象,而以具體的文學作品為主)為對象的評價和研究活動。
首先,文學批評具有獨立性。批評是一種建構,一種再創造。任何一位文學批評家都不否認他對創造性的追求。正如法國文學批評家蒂博代所說:“所能給予一位大批評家的最高榮譽是使批評在他手中真正成為一種創造。”批評家依據一定的批評觀念、方法,首先對批評的對象進行選擇,然后著力于發掘、揭示所批評作品的內在價值,這是一個建立在對作家與作品充分理解基礎上的重新建構、新的綜合過程,即對作品從“理解”進入“發現”,發現作家未意識到的作品的價值水平以及作品的潛在意義,并以獨特的審美理想進行再創造,這時,批評家在批評中表現出自己獨特的審美理想、審美觀念,使自己的批評也成為一種凝聚著審美個性的“創作”。有了這種創造意識,批評家就不僅是作家的知音而且是與作家并列于文學王國中的另一種意義的作家。另外,文學批評必須在聯系于哲學、政治、道德、歷史、文化等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擺脫成為它們附庸的重負;必須在聯系于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同時也改變成為它們附庸的地位,而應該使批評回到批評自身的本置中來,使批評真正成為批評.,成為“文學”的批評。
其次,文學批評具有科學性。文學批評不是對主體情感體驗的簡單記錄,而是一種轉換,“批評其實是從感覺的范圍轉到思想的范圍。”體驗的心理學含義是“從內部”加以知覺,使主體的藝術知覺變為對現實生活的情感認識。而批評則是從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看待對象,在內部體驗與外部觀照和思考的結合中對對象作出綜合判斷。判斷意味著文學批評應在對文學作品及現象的感受中探尋和揭示這些現象內所蘊涵的普遍規律和真理。在發掘和研究文學現象與規律之關系的工作中,僅憑批評者個人的喜好與情感偏向還遠遠不夠,理性化的思維方式是必要的。與此相關,在表達方式上,文學批評應盡可能明確、坦率,這樣才能符合批評家理性思維的軌跡,完成批評所應擔負的態度鮮明地表述觀點、評判作品的任務。這一點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批評應當是盡可能避免任何半吞半吐,限語但書,細致而暖昧的暗示以及諸如此類只能妨礙問題的率直、明朗的迂曲說法。”
另外,文學批評注重對方法診的探索。進入20世紀以來,批評對方法論的探索熱情與何比重明顯增加,批評家自覺的批評意識與某種或數種科亨法或學術思潮相結合,產生了如精神分析批評、原型批評結構主義批評、現象學批評、讀者反應批評等多種形態和流派。這種狀況顯示了文學批評尋求秩序和建立系統的一種愿望,以使批評變得更加科學化。加拿大文論家諾思洛普·弗萊說過這樣一段話:“不論涉及哪一領域,科學的引入都會使秩序代替混亂,在原只是偶然和直觀的地方建立起系統來,同時它還保護了這一領域的完整,使它免遭外部侵入。”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對20世紀文學批評科學化走向的一個說明。建立在新的哲學觀念以及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乃至自然科學理論基礎上的新的批評方法的引入,為拓展批評家的思維領域,豐富和完善批評手段,從而推動整個文學批評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隨著批評方法的確立和批評模式的建構完成,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因素更加得到增強。
文學批評的理論化。從文學批評來看,當其擺脫傳統的理論附庸地位,通過具體文本分析而在文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大顯身手時,本身已經擔當起新的理論先鋒角色。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莫瑞·克里格說:“作為一種知識形態,而不是僅僅作為我們與文學的情感遭遇的詳細描述,文學批評必須理論化。”正是這種理論化的批評使得“理論的作用業已深化和廣泛”。當今的文學批評與傳統的文學批評已有了很大的區別,它們所關注的重心不再是一些具體的文本,而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性質、目的、對象和研究方法等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即使面對具體的批評對象,批評家們也主要不是以情感和審美為基礎,而是以思辨的方式,在一定理論框架的規約下,運用一套理論范疇對文學作品加以剖析。20世紀文學批評十分注重理論建構,它們大多是通過某種理論預設,在演繹的框架中推導而成。在對已存批評的反思中,批評家也總是從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人手,以否定其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同時試圖在理論上有所開拓,有所建樹。而在理論建構中,20世紀的文學批評又表現出一種泛學科的趨勢,即通過與其他學科的聯姻,在借鑒其成果的基礎上形成特有的理論框架。在20世紀,幾乎沒有一種文學批評不與其他學科發生關系。結構主義文學批評正是從現代語言學中獲取了靈感,精神分析批評本身就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產物,而文化學批評則借鑒了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這些人文學科的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堅實的學科背景,成為各種文學批評流派的理論前提。當今的各種文學批評正是通過對這些學科研究成果的引進、消化和吸收,在交叉、邊緣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套套獨具特色的理論主張和觀念方法,使文學批評呈現出濃郁的學術氛圍。這種聯姻不僅加強了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和特色,多方面地揭示了文學的本質,同時也擴大了文學批評的關注范圍,將文學批評研究的問題擴展到與文學相關的文化和知識的前沿。
 購物車(0)
購物車(0)